目录
快速导航-
特别推荐 | 星辰与谜语
特别推荐 | 星辰与谜语
-
特别推荐 | 牡缅密缅
特别推荐 | 牡缅密缅
-

特约专栏 | 灯笼树下
特约专栏 | 灯笼树下
-
作家视野 | 一种与书写相关的时间标本
作家视野 | 一种与书写相关的时间标本
-
作家视野 | 在烟垄间
作家视野 | 在烟垄间
-
作家视野 | 美国琐记
作家视野 | 美国琐记
-
作家视野 | 原本山川,极命草木
作家视野 | 原本山川,极命草木
-
性情写作 | 雪中的南太行
性情写作 | 雪中的南太行
-
性情写作 | 河流之上
性情写作 | 河流之上
-
性情写作 | 雪泥鸿爪
性情写作 | 雪泥鸿爪
-
别具只眼 | 野外之心
别具只眼 | 野外之心
-
别具只眼 | 时间的体温
别具只眼 | 时间的体温
-
别具只眼 | 心里流淌一条大河
别具只眼 | 心里流淌一条大河
-
别具只眼 | 螺蛳记
别具只眼 | 螺蛳记
-
人与自然 | 留在山野中的歌声
人与自然 | 留在山野中的歌声
-
人与自然 | 咸酱豆 腌萝卜
人与自然 | 咸酱豆 腌萝卜
-
海天片羽 | 岁月深处的乔厂长
海天片羽 | 岁月深处的乔厂长
-
海天片羽 | 青梅
海天片羽 | 青梅
-
海天片羽 | 返回与遗忘
海天片羽 | 返回与遗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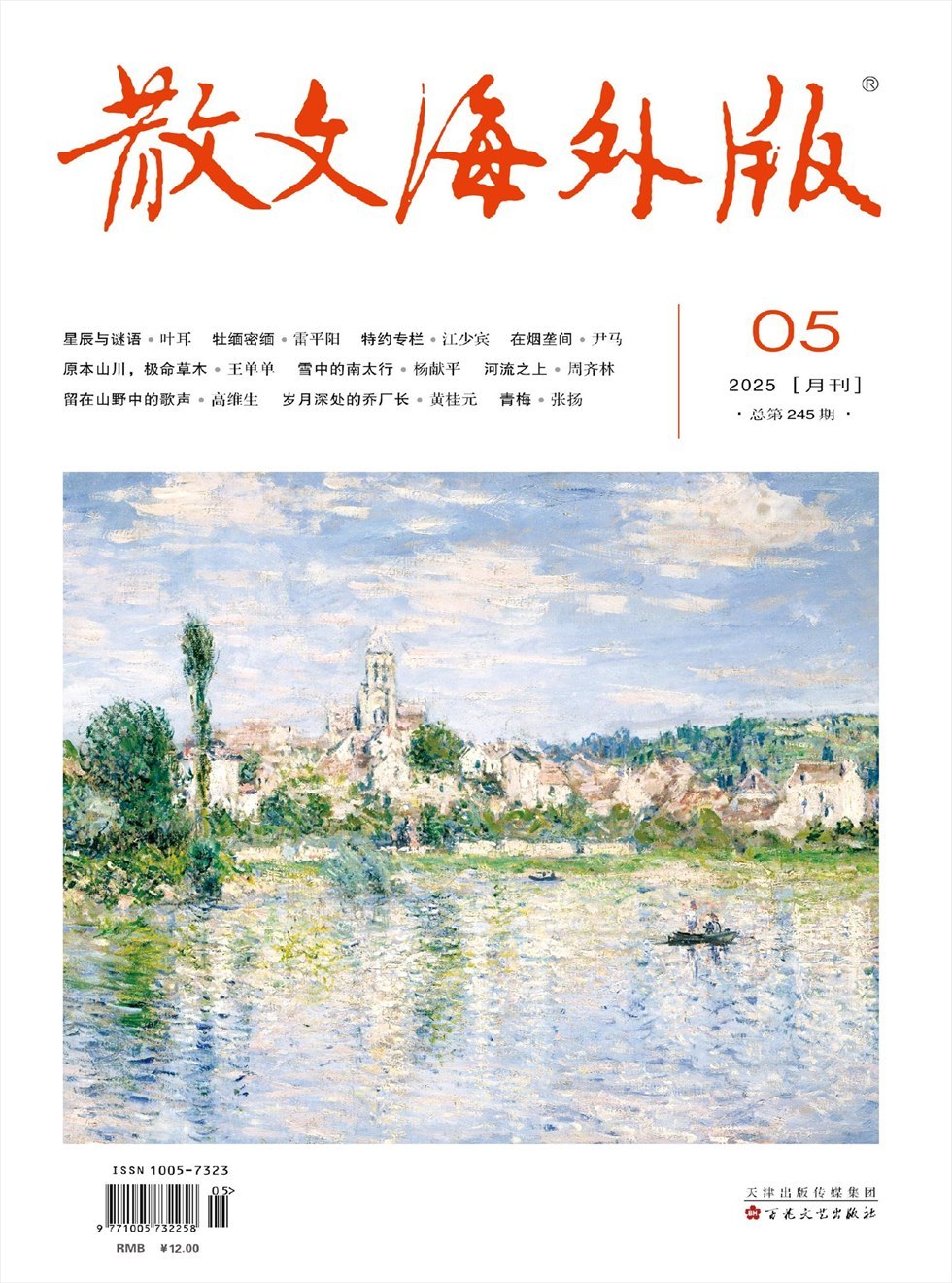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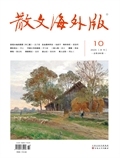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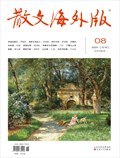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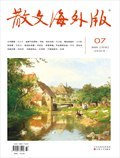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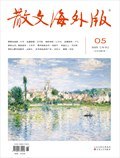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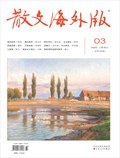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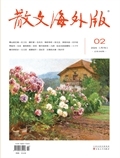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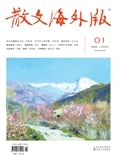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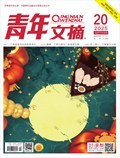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