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全部分类/
- 文学文摘/
- 小品文选刊·印象大同
 扫码免费借阅
扫码免费借阅
目录
快速导航-
卷首 | 生命的本质
卷首 | 生命的本质
-

城坊 | 远去的故乡,是灵魂的巢
城坊 | 远去的故乡,是灵魂的巢
-
城坊 | 炒米胡同里看夕阳
城坊 | 炒米胡同里看夕阳
-
城坊 | 西安二题
城坊 | 西安二题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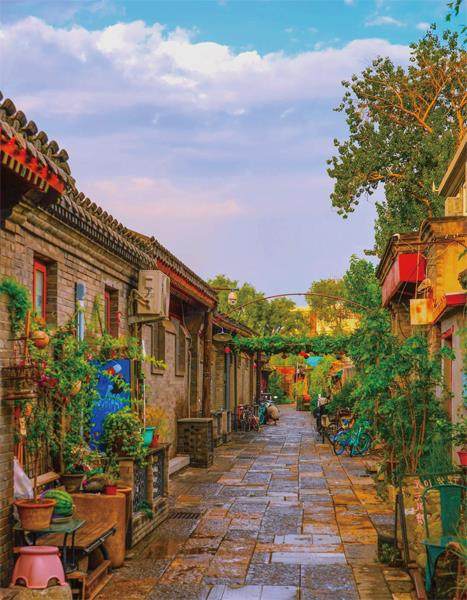
城坊 | 小胡同里的北京味
城坊 | 小胡同里的北京味
-

百态 | 最好的父子关系是什么样
百态 | 最好的父子关系是什么样
-

百态 | 洁癖
百态 | 洁癖
-

百态 | 谁能笑到最后
百态 | 谁能笑到最后
-
百态 | 永远不搬家
百态 | 永远不搬家
-
视野 | 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
视野 | 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
-

视野 | 淡烟疏雨落花天
视野 | 淡烟疏雨落花天
-

视野 | 道路以目
视野 | 道路以目
-

视野 | 苏东坡与爱犬
视野 | 苏东坡与爱犬
-
感悟 | 我的双手
感悟 | 我的双手
-
感悟 | 外婆的名字
感悟 | 外婆的名字
-

感悟 | 落在母亲身上的雪
感悟 | 落在母亲身上的雪
-
知道 | 《文心雕龙》究竟因何不朽
知道 | 《文心雕龙》究竟因何不朽
-

知道 | 人为什么要去旅行
知道 | 人为什么要去旅行
-
知道 | 如何辨认身边的聪明人
知道 | 如何辨认身边的聪明人
-

思维 | 人文学者:怎样与AI共舞
思维 | 人文学者:怎样与AI共舞
-

思维 | 风筝线的记忆
思维 | 风筝线的记忆
-

思维 | 保持好心情的锦囊妙计
思维 | 保持好心情的锦囊妙计
-

边声 | 我在故乡捡歌
边声 | 我在故乡捡歌
-

边声 | 家乡的苦菜
边声 | 家乡的苦菜
-
边声 | 细喃
边声 | 细喃
-

边声 | 剪不断的土窑情
边声 | 剪不断的土窑情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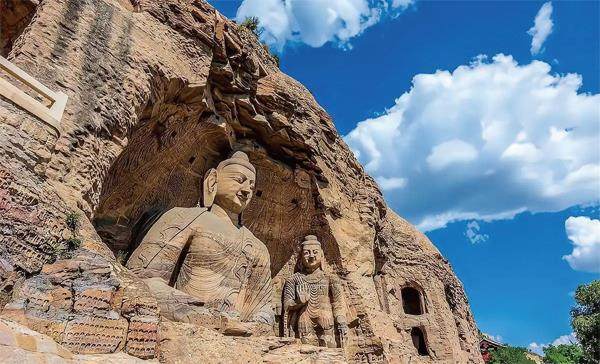
大同大不同 | 云的冈 石的窟
大同大不同 | 云的冈 石的窟
-

大同大不同 | 千年车辙里的文明交响
大同大不同 | 千年车辙里的文明交响
-

大同大不同 | 家门前的“西环路”
大同大不同 | 家门前的“西环路”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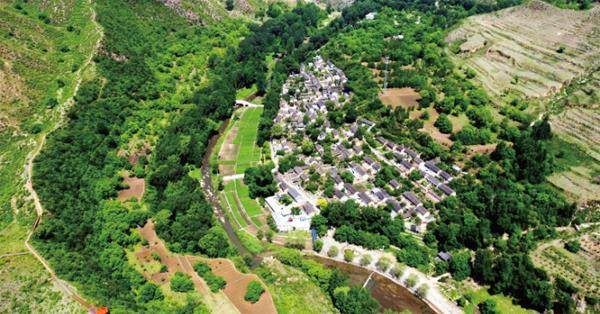
大同大不同 | 花塔 花塔
大同大不同 | 花塔 花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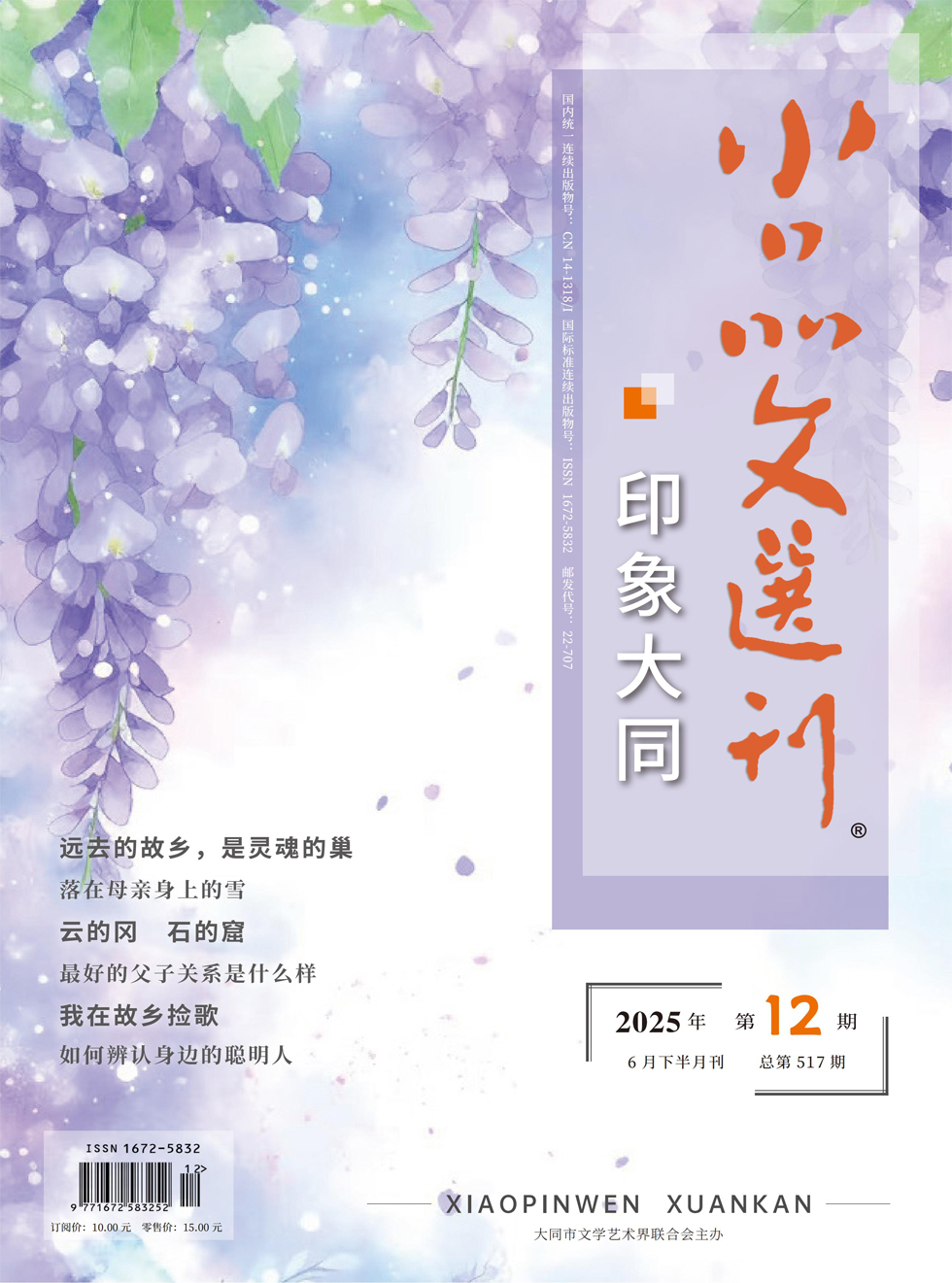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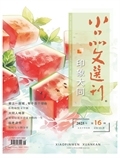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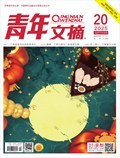





 登录
登录